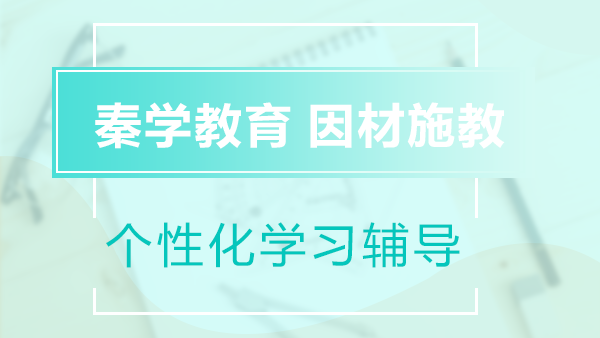| 组别: | 高中组 | 班级: | 四川-眉山-彭山县-彭山县第一中学八班 |
| 姓名: | 时可 | 指导老师: | 杨静 |
| 赛区: | 四川 |
山中私塾
二十年前,湘西以南的禛江镇上一间老宅被人收买。买客是一位四十上下的男人,头发油亮,两鬓梳得干净利落,戴个旧时圆框眼镜,上衣深蓝中山装,下身棉麻裤,身板挺直,一身正气。镇子上有条溪流,大约二十丈深,河床以白石为底,在溪边不远处便有个码头。每天天还未舒展成铮亮时,码头上遍挤满了人,拴在马脖上得银铃声与人的嘈杂声充杂在各种牲畜和谷物间,渡船顺着溪流上上下下。溪流顺山而岨,弯如弓背,山又弯如弓弦,在弓背与弓弦之间,便是那间屋子。
这屋子是个四合院,房屋原来的主人在抗日战争时某天夜里悄悄出离,而后几十年镇上的人也未闻他们的音讯,于是这屋子也就在此空了几十年。屋后是一山茶峒,檐角尽被绿藤错杂盘绕,窗户上也被灰尘覆得不透光影,屋内摆放如旧,院子也尚冷清,悄怆幽邃,空空荡荡。
那男人姓沈,名拓,赣州人,是个教书先生。他来的一个月后,让这古朴的屋子完全变了样。堂屋摆放着大约二十方檀木做的方桌与红乔制的木椅,靠墙的地方有个讲桌,壁上的粉漆被蹭了些许下来,左右各挂着一副字画:闰逸庭松露湿衣,偶题岩石云生华。门楣上裱了四个大字:禛水私塾。院子里移栽了几株茶山菊和翠竹,与后山的茶峒熠熠相映。
天才朦胧,镇上的人便稀稀落落的摞着担子从官路穿过到码头上去。妇女们盘坐在溪边,身旁放着着棒槌与皂角,双手浸入冰澈的水中涤洗衣物。她们都不约而同的谈论到那个新来的男人。“哎,你听说没有,那个个把月前来我们的那个人,在茶峒边上建了个私塾。”“可不是么,听说还不收钱嘞。这下嘛家那人也就没啥可在我们面前吹嘘自己儿子念过书哩。‘’
禛江祖辈大多曾是清朝有名的工匠,后来被小人诬陷在修筑园林时贪赃,到底被乾隆罢了职务。于是便带着乡人远迁湘江一带,祖辈们依山凭水筑城,临水一面留出空地设码头,湾泊小小蓬船。乡人远离世俗,大多都不曾认得几个字,在这之前镇上没有教书先生,稍富贵的人家会送孩子去湘水下边的月城念书。娃子自打生下来就喑在这潺潺溪涧之中,跟着爹在水路之中上上下下贩卖杮子与江盐制品,丫头随着娘做些针线活或捣捣杏花搓桑麻。
没隔几日,那宅子便坐满了人。第整天他向孩子们讲了自己的故居与经历,告诉他们叫他沈拓便好。后来几天,孩子们陆陆续续的拿到课本——一本本宣纸裁成的矩形小册子,厚度约两寸,里面有鲁迅的杂文,也有冰心的短诗,有革命烈士的诗歌,也有先贤报国的词篇。
每逢他给学生们讲到鲁迅的小说,他总逐字逐句的分析,怀着激动的感情向学生们涌述文章背后对时政与侵略者的评判,当讲到抗日烈士的诗歌时,他总不自已的放慢声调如诵经般反复诵读,有时眼圈甚至会变得微红,甚是发出哽咽的声响,学生们也默不作声,静等他收整好情绪。
多年后,禛江镇的房屋全都又抹上了一层乌黑的亮瓦,家家户户的门外的篱墙上尽贴着幅朱红的对联。临水的些蓬船也都翻了新,站在江岸的商客们头顶嘴巴拗的飞快,娴熟的仔拨算货物之间的价钱。当年那些俊俏的小姑娘们也成了人妇,坐在其宅院之中抱着尚允乳的孩子教他们识字算数。沈拓一如既往的住在茶峒边的宅子之中,二十年间,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它们之中有的做了军人,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大夫。他从黑发成白发,从中年成老年,岁月如刀刃般在其额前磨出刀刀沧桑的痕迹。
二十年间,不断有人问为何他来此教书,且这一教便是二十年。他每次都婉婉而谈,二十年来也没人弄明白透过。
三个月后,沈拓突患了疟疾,卧在床前不起,且咳嗽时还有贞贞血丝。镇上的人一连十多天都为看见他,便估摸着出了什么事,都纷纷前去看个究竟。当年他的学生知道这事后,连夜渡船从上海赶来为其看病,就连那些早已远迁他乡的镇上人,甚至是每天忙于商贸的也都前来齐围在沈拓的床前。
院子还是他刚来的那般模样,堂屋前的那株纸竹尚在往上拔,庭院里的海棠花开花落,却也添了几分憔悴的姿色。天气转凉,沈拓的病更是加剧,为他把过脉的大夫告诉镇上人说沈拓已病入膏肓,只能合着草药能活整天是整天。他的学生们不信,四处打听有名气的大夫前来为沈老看病。
又过了几日,禛子上回来了一个人。是沈拓的养子,也算是这镇子上与其较亲近的人。父亲是一名烈士,母亲在其出生时便已故,沈老得知后便把他领养,待他如自己儿女般亲切。看见沈拓如今这般模样,他内疚的跪倒在他的床前,一连自责了几天,于是他告诉镇子上的人们,其实早些年,沈老常常在月色下独自去后山的茶峒之中散心,他说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又有宿命的必然。他曾希望如果有整天自己离开了,能将它安葬在这茶峒之中。
那整天终是到了。他的屋子里外都是人,沈拓艰难的用右手支撑起身子,伸出左指向堂屋壁便的一个抽屉指去,他的学生们明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沈拓也点了点头,笑了笑,便一躺再也并没有醒来。他的学生们悲恸的按着沈拓的意思打开那抽屉。里面是一本相册。他么翻开它,里面夹满了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每张上面都是三个人——忽然一位年岁尚高的老人从后面挤了上来,他眨了眨眼,又盯了盯照片,说道:“这,这不是当年这间宅子较初的主人吗,我记得他们的模样,那男的留了一个八字胡,头发往两边撮,听说是个激进的革命家;那女的爱穿蜀绣的旗袍,发间串了根泰蓝木暨,大抵是他的妻子。“然后呢?”另一个学生问道,“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那男人主张变法,反对蒋介石对日寇的消极政策,他主张国共联合积极抗日,当时镇上的许多人都响应了他,加入到这队伍中来,可不知谁在其间背叛了他,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全部牺牲,只剩他苟延残喘的回到村子。接后的几天镇子上的人觉得是他害了整个村子,是个灾星,誓言要把他杀了以示死去的村民。于是便把他绑了起来,三天后,在镇上的集市中央处以绞刑。我依稀记得那时有一个女人与个小男孩站在较前面,那孩子使劲的哭喊,女人一边用手遮住了孩子的双眼,一边也在不停的哽咽。后来,那宅子里的大半东西都被搬了空,成了一间死宅。
忽然从相册后几页掉了一封信出来,虽已破烂褶皱,但字迹尚能辨析清楚,他们小心的打开它,上面写着:
拓儿,你的身体是否康好?自你在洋求学以后,我也难再与见面与交谈。母亲我的身子也是整天恶于整天,也许快要走到生命边缘了。拓儿,那么多年了,我不知你是否放下了当年对禛江百姓的仇恨,世事变迁,我看淡了世间苦楚百态,你父亲在身前曾对我说其实这些人们并不是愚昧麻木之人,他们只是未曾受到开化,没有一顿觉悟罢了,若他在天有灵,我估摸着他定愿看见禛江镇的人能真正走出封建的束缚,以兴亡未为己任,以民族衰败为使命。孩子,放下当年的怨与执念吧,那里毕竟是我们仨的根,就请归去了了你父亲生前的心愿罢。
“原来沈老这么做是为了,为了——”说话的人打住了,随后变得缄默,于是整个屋子也变得缄默,如烟杪朦胧般的弥漫着压抑。
几天后,在那后山的茶峒之中围满了人。人们簇拥在半峒间的一块低矮的地痞间。镇上的人如了沈拓的愿,把他葬在了这茶峒之中。
多年后,一个孩子牵着母亲的用手指着那茶峒说;“娘,这茶峒好美呀”
“是啊,这么隽秀的茶峒,沈拓大抵也放不下吧。”
“沈拓,沈拓,他是谁呀”
“他呀,他是咱们禛江镇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