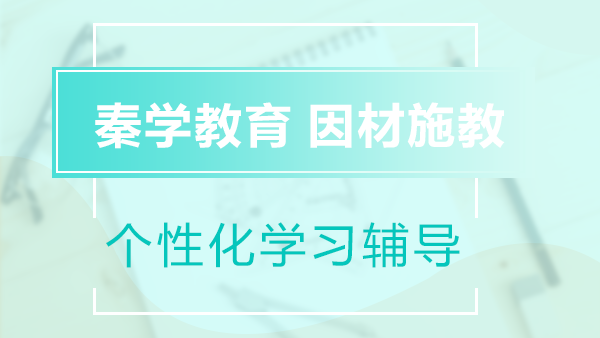闲亭雅坐,他吐出青烟,娴熟自然,如呼吸一般。泡上一壶浓茶,端着壶底,一手抓着壶柄喝了一口,眯着眼紧锁眉头,在似火一般的荷花簇拥下,活似一位逍遥快活的仙人。
他姓何,是位教授。

每当我毕恭毕敬地尊称着“何教授”时,他总会像小孩一般地恼怒,用手指叩着我的脑袋说:“叫老何!臭小子!”他这人是极有趣的。他爱车,但并不爱惜他的车。一辆普通的三菱面包车——锈迹斑斑,风尘模糊了它的样子。也许是厌烦了讲学的束缚,他总是操起了“向导”的行头。他会开着车带着外来的旅人在川西北转悠,与藏民同吃同住,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同他们交流。老何人送外号“川蜀活地图”。只不过每次如此唤他时,他总是露出一口大黄牙摆摆手说:“瞎说,一个糟老头子能记多少哩!”
一次在驿站,海拔四五千米。冰冷的寒风夹裹着高原独有的干燥穿透进皮肤,刀扎一样,肆意妄为地挑战着我们的生理极限。我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露出半点地方让风有机可乘。老何停好车后步履稳健,潇潇洒洒得走进来。先是从包里掏出一只水壶,直奔洗手间“簌簌”地接了满满一壶水。然后又倒腾着拿出他那一套宝贝般的茶具,小心翼翼地烧上水。随后他大刀阔斧地把身上的衣服一扒,不拘小节地把他硬朗的身材展现在我们面前,粗重地呼着气向前一倒,双手稳稳地把身体撑起来,真汉子一般做起了俯卧撑。待到他身体冒汗,面红耳赤时,他迅速弹起,往浴室里奔。令我震惊的是,我丝毫看不到浴室中热气的蒸腾——在这样的环境里洗凉水澡的能找出几个?不一会儿,他穿着裤衩便冲了出来,在他脸上我看不到的痛苦,我看到的是一个真男人的硬气!他迅捷地往床上一跳,拉扯着被子将自己紧紧包住,一边掏着衣服口袋里的香烟,一边抓着泡好的绿茗。一口热茶顺着他的喉咙向下倾流,在胃里滚动着,驱散了寒冷。他犀利的目光锁定了我,用眉挑了挑示意我。我知趣地在床头拿来打火机,为他点好了他已经叼在嘴里的香烟。只见他自在地吐出烟圈,又是一口热茶入肚,两股热流在身体里回荡交织,用凡人之力抨击着自然带来的极寒。“何教授,得劲!”我崇拜地望着他。“破老头子我还想多抽几年烟,多饮几年茶呢。”老何憨憨地回答道。他彻底成为了我的偶像。
他喜欢和藏民们打成一片。他喜欢接客去藏民家做客,一进藏民家就如同在自己家一般,毫不生疏地同他们唠唠家常。虽穿着同藏民们格格不入的军绿色大衣,但他总是能融入其中。馋嘴的我们早就对牦牛酸奶垂涎三尺了,老何似乎洞悉了我们眼中的馋光,带我们来到一家极具藏族色彩的小平房里。用藏语流利地和女主人交谈着什么,也许是在寒暄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位穿着暗色长袍的小哥脸上附着高原红端着几碗酸奶径直走了进里屋。
小哥操着带有藏语独特节奏的普通话含羞对我们说:“客人们,慢用。”我双手接过道了声谢,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滑嫩诱人的酸奶,狼吞虎咽般饕餮大餐了起来。
“嘎玛,你家的奶,香!”老何竖了竖大拇指。女主人客气地笑了笑:“我家男人进城的工作还是麻烦您找的,真是谢谢您了。”“小事,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们为我接待客人也帮了不少忙哩!”老何咧开嘴像孩子一样笑道。“我们村里男人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您给介绍的。您是高级知识分子,为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哝。”老何摆了摆手,笑着自嘲道:“不是知识分子呢,不是呢。支持的扶贫政策也是应该的。”说完,便张嘴大笑露出一口大黄牙来。他那与民相近的乡土气质甚至一时让我忘了他还是名学识渊博的教授。
忆起他,总是忘不了他不同于身份的气息。虽许久未见这位有趣的老人,现在的他是否还在路上载客进藏同民相处,吞吐着他的香烟,带着责怪的语气教训年轻人对他的恭敬。我爱这个怪脾气的老头!